在成都平原四千多年的人类文明中,体育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所推崇、所热爱。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不仅承载了成都先民的生存智慧,也生动地反映了成都先民安逸闲适的生活。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文物、古籍,窥探一二。
渔猎攻战纹铜壶:射箭最普及

嵌错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 四川博物院收藏
射箭是我国的传统运动项目之一,其历史悠久。在人类社会早期,为了生存,人类不仅要猎取食物,还要防御野兽的侵袭。因此,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逐渐发明了弓和箭。
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距今两万八千年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发现了一件燧石镞头,是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的,尖端周正,肩部两侧变窄似铤状。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箭头之一。
蜀人的祖先最开始居住在岷山山脉深处,主要以捕猎为生,弓箭也成为他们的重要工具。而后,他们从岷江河谷的汶茂盆地向东南而下,经过彭州市北部,到达现在的彭州市小鱼洞镇一带,这里多水泽,盛产鱼,土地也相对肥沃,因此“鱼凫王田于湔山”,其部落也开始了由游牧向渔猎再向农耕的转变。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雕刻着一张弓箭、一条鱼和一只飞鸟,鱼被弓箭贯穿而入,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三星堆金杖上。这样的图案应当是当时人们使用弓箭渔猎的一个场景再现。金是古代的重器,将这样的图案刻在金冠带、金杖上,可见弓箭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箭镞与骨质箭镞,正好说明了古蜀人在原始渔猎生活中频繁使用的射箭技术。
当古蜀人进入农耕社会后,农耕取代了渔猎,但弓箭的使用仍然在延续。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件“嵌错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该壶通体刻有纹饰,纹饰分为四层,第一层为“习射、采桑”;第二层为“宴乐、弋射”;第三层为“水陆攻战”;第四层为“狩猎”。这些纹饰铸造精美、内容丰富,且每一层纹饰都与射箭有关,生动再现了古蜀人使用弓箭的场景。
射箭不但能增强臂力,扩张胸围,增进目力,还可以培养人沉着、果敢的精神。因此,射箭这一远古社会必不可少的生产实践活动,在经历漫长的文明演化后,逐步成为《周礼》中记载的作为修身养性与培养君子风度的“六艺”之一。最终,演变为现代大众健身、娱乐方式的射箭运动。
水戏图:耍水名堂多
成都平原水系发达,河流众多。因此,蜀人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与水发生着关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游泳技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上的需要,促使各国加强了水军的扩大和训练。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中出土的“嵌错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第三层纹饰就刻画了“水陆攻战”的场面。
当然,游泳在我国古代不仅用于生活、军事中,还作为一种娱乐活动。1972年郫县竹瓦铺的汉墓中出土了一具石棺,其上刻有一幅“水戏图”。图中,左为莲池,小舟上立一鹤,有二人摇桨,一人展力叉鱼,池内有鹤、鱼、蟾蜍、莲等;中部左起第一人执伞站立,身前五人,中者高冠长服,手捧乐器站立,旁四人捧盾躬身作迎候状,右侧树二旗,旗间四人并列,四肢着地,背朝上,似作比赛状;身后一人执建鼓,上有华盖,身体微微向前,举手欲击建鼓为其助兴。这幅图中,游泳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浮水技能,而是发展为复杂的水上表演技艺,供人们观赏、娱乐。
打马球:天子百姓齐上阵

《明宣宗行乐图》中描绘的明朝王公贵族打马球的场面
当我们走进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不免会被一件砖雕吸引。这件砖雕就是宋代的“打马球砖雕”。砖雕呈正方形,边长29厘米。浮雕着一个戴簪花幞头的男子,他身着圆领长袍,腰束带,衣袂飘飘,鸾铃叮当,骑一鞍具华丽、矫健奔驰的骏马,手持似月的杖杆,欲挥杆击球。整个砖雕雕工精致,栩栩如生,一下子就能将我们带入千年前宋代紧张、刺激的马球运动中。
马球古称“打球”“击球”“击鞠”,与蹴鞠、捶丸同称为中国古代“三大球”。关于马球的起源与传承,目前尚有争论。有学者认为马球起源于古波斯,后传入吐蕃,隋唐时传入长安。不过目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古人在东汉时期就自创了马球。其依据是曹植的《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诗句,描写的正是“京洛少年”行猎归来,宴饮之后,到马球场地打马球的场景。
马球运动在唐代尤为兴盛。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吐蕃赞普派大臣尚赞咄等至长安迎接金城公主,因知大唐天子酷爱看马球比赛,便带来一支马球队,要与汉人进行一场“友谊赛”。吐蕃是游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室的神策军马球队与之比赛,数战皆输。唐中宗李显十分懊恼,便命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一起,临时组成一个“超级战队”,上场与吐蕃队一决高下。开赛之后,李隆基策马奋杖,“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队望尘莫及,只得认输告败。中宗挽回了颜面,欣喜异常,赐绢数百缎。
唐末的僖宗对马球的喜爱较唐中宗、唐玄宗更甚。这位皇帝自封“马球状元”,黄巢起义爆发后,他入蜀避乱,每天依然必打马球,其场地大概在今天府广场的位置或大慈寺前、华西坝上。这样,成都老百姓也能一睹一国之君打马球的风采。正所谓上行下效,每天看唐僖宗打马球,成都老百姓也耳濡目染,马球很快在成都流行起来,成为当时成都市民喜爱的一项娱乐、体育活动。
前蜀高祖王建也酷爱马球,他在成都称帝后,要求重建马球场,除了满足马球场的基本条件,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历史上最奢华的马球场。据《资治通鉴》记载:“蜀主常列锦步障,击球其中”,也就是说王建用珍贵的蜀锦代替原来的土墙作为马球场周边的屏障,以防止马球飞出场外。这样奢侈、任性的做法实在让人惊叹!
舞剑画像砖:一舞剑器动四方
剑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重要的武器。到了汉唐,由于骑兵的发展成熟和在战场上的广泛使用,剑在战场上失去了它的作用。曾经被人们争相研习的剑术,也逐渐转变为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的舞剑了。虽然不再是用于争战的击技,但舞剑还是讲究招法的,它寓技击动作于运动形式之中,所以既能习武健身,又能观赏。
1976年,成都金堂县出土了一块汉代“剑舞”画像砖,图中的舞剑者头挽双髻,着紧身舞服,细腰束带,昂胸跨步双剑齐舞,造型优美。更难得的是,当时的舞剑者一般是男性,而这块画像砖中的舞剑者是一名女性,这是画像砖中绝无仅有的。
巧合的是,数百年后的唐朝,“诗圣”杜甫又亲眼见证了这样精彩的表演。杜甫在他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写道: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
这是唐大历二年(767年)十月十九日,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时,回忆起开元三年(715年)在郾城观其师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情景。通过杜甫的描述,剑的声光,似闻如见。公孙大娘精湛的技艺,舞剑时惊心动魄的气氛,如呈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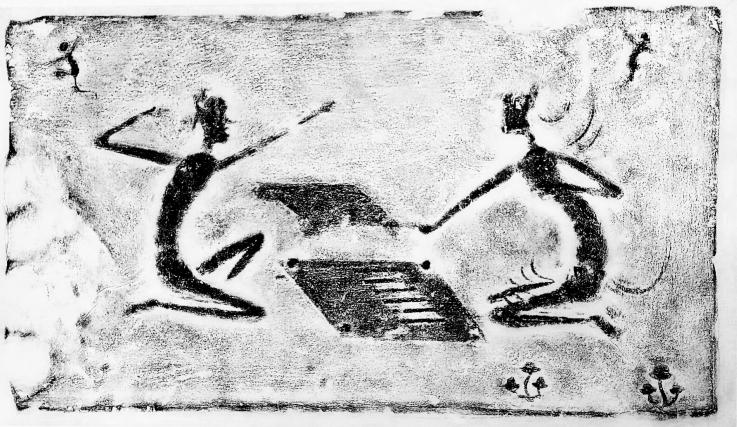
仙人六博画像砖拓片
击壤而歌:失传的盛世游戏
明朝着名文学家、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杨慎着的《俗言·抛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宋世寒食有抛堶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若今之打瓦也。”什么是“抛堶”,什么是“打瓦”?这还要从另一种游戏--击壤说起。
三国魏邯郸淳《艺经》中有记载:“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这说明在古代,击壤是一种有比赛、分争高低上下、力求准确性的投掷运动。
击壤的产生大约与远古时代人类的狩猎活动有关。那时,人类用木棒、石头击打野兽。后来,狩猎的工具有了极大地改进,弹弓、弓箭等工具的发明让人类放弃了原始且低效的木石投掷,让它逐渐演变为人们休闲时的游戏。
据西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壤父》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虽然壤父的话反驳了旁观者“击壤体现尧的大德”的说法,但壤父能够衣食无忧,安然击壤于道中,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尧的治理有方。因而,“帝尧之世,击壤而歌”成了后世歌颂太平盛世的典故。
两晋南北朝时,击壤在民间非常流行。西晋文学家张协的《七命》中有“玄龆巷歌,黄发击壤”之句,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儿童和老人在巷中放歌、击壤的其乐融融的景象。南朝诗人谢灵运也在他的《初去郡》诗中写道:“既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抒发自己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
后来,大概是因为击壤这种游戏过于单调,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它逐渐发展为击砖、打瓦等游戏,人民用砖、瓦代替了壤,并完善了比赛的规则,增加了其游戏性。
画纸为棋:离乱后的幸福生活
围棋,起源于中国,我国古代称为“弈”。相传围棋是尧发明的,先秦典籍《世本》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经相当流行,孔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西汉着名文学家、成都人扬雄也在其《方言》卷五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
三国时期,蜀国多有争战,自然需要一些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领、谋士,围棋似乎成了他们演练的工具。由此,围棋也在成都兴起来了。出土于成都市大邑县的魏晋“六博画像砖”,其上刻画的就是二人对弈的场面。
“诗圣”杜甫也喜欢下围棋。流寓蜀中时,得朋友的帮助,杜甫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作为安身之所。茅屋建成后,杜甫作《江村》一诗,其中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之句。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想象,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杜甫终于获得了一个安居的栖身之所,生活暂时得到了安宁,妻子儿女同聚一处,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年幼的儿子用稚嫩的小手一点一点儿将钢针敲作钓钩,准备到浣花溪上垂钓,夫妇二人则苦中作乐,“画纸为棋局”。这既反映了离乱甫定时生活的艰辛,也足见他们旷达、愉悦的心境。(文 江夏)


